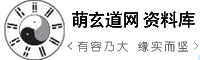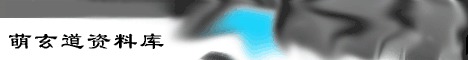近三十年来《老子》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述评——兼与韩国良先生商榷
| ”重新句读为“故有,无之相生也”,并译为“有是由无生出的”。这是对《老子》中有、无观念的进一步误解。因为“有”与“无”在老子哲学中有不同层面的理解[11]。如第1章的“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讲“有”、“无”。而第11章中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的“有”与“无”分别指形而下的事物之实物与虚空。回到第2章中的“有无相生”,这里的“有”与“无”在句中的地位是对等的,并非韩先生理解的“有是由无生出的”。韩先生的误读首先基于老子哲学以“无”为本的所谓一元论观念的驱使,其次乃是由于不了解古汉语“相”这个词的用法。马建忠认为“相”是“互指代字,必合动字,以明其互为宾主也。盖动字之行,有施有受,施者为主,而受者为宾,故有宾主之次互指代字”[12]。王力先生肯定了马氏的说法,并认为“自和相都是反身代词,用作状语”[13]。“相”作为互指代字或反身代词,不能独立使用,必须指代具体的对象。在第2章中,“相”正好处在动词之前,其实是对“相”之前两个名词的指代,并且这种指代是互指,因而“有”与“无”在句中“互为宾主”,既是宾语又是主语。因此,“有”与“无”的地位当然是对等的,谈不上谁更根本。
再如韩先生提到今本第27章的“善人者,不善人之师”,而帛书乙本作“故善人,善人之师”。高明根据韩非子的《喻老篇》考证韩非所据《老子》的文本中应该作“善人之师”[14],可证帛书乙本中“善人之师”的说法渊源有自。韩先生将其断为“善人善,人之师”,姑且看作是另外一种理解,却不能以此否认学界的其他解读尝试,更无法得出“帛书此章提供的异文也同样没得到注意”的结论。 最后,韩先生将第2章“为而不恃”释读“化而不恃”。这里的“为而不恃”之“为”与“处无为之事”的“无为”是否矛盾?如果认为老子之无为即无所作为,放弃一切作为,那么理所当然地会得出两者矛盾的结论。很可能韩先生持此论并且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要顺畅地解读此章,关键还在于理清这段经文的主词问题。通常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作”的主语是万物,除此之外,“生”、“弗始”、“为”、“弗恃”、“成”、“弗居”的主语均为圣人[15]。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为、成三动词的主词皆为‘万物’,而‘弗始’、‘弗恃’、‘弗居’的主词则为‘圣人’”[16]。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圣人是整个句子的主语,而从第三句开始,万物与圣人的行为一先一后交错,即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按照其本性自生自长,而圣人对万物的生长发育并不干涉,采取的是“弗始”、“弗恃”、“弗居”,这些否定词也正好体现了“无为”的观念[17]。笔者揣测,韩先生认为“为而不恃”乃“化而不恃”之误,应该是为“万物”这个主词寻找一种合适的行为,而不是为“圣人”寻找一种合适的行为。因为“化”即便理解为圣人化育万物的行为,也仍然是一种“为”,所谓的“矛盾”依然存在。至此,韩先生提出的释读尽管不妨看做一种理解,但笔者认为这种基于所谓“矛盾”而进行的解读并无意义。 以上我们简要地考察了学界近三十年来对《老子》文本考证(前两个方面内容)所取得的成绩,并且重新分析了韩先生提出的几个文本考证例子。显而易见,韩先生所举之例根本无法得出学界在《老子》文本考证上停滞不前的结论。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老子》文本考证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很多字词的释读和考辩仍然有待深入。而在《老子》文本考证上亦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过于追求《老子》文本的完整性,希望借助简帛《老子》化解通行文本中的内在矛盾,塑造一个完整的《老子》古本或善本。诚然,文本的校勘与考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肩负着这个目的,但对于复杂的《老子》文本来说,强烈的求善本目的驱使极易导致种种误解,而忽视《老子》文本流传中的思想演变问题。显然,竹简本只是目前最古老的传本,但还无法确证是原始的、完整的传本。事实上,《老子》文本有一个不断流传、转抄的过程,可以说战国中后期《老子》文本的流传绝非单线条的,而是存在多种流传本。竹简《老子》、帛书《老子》以及通行本的一些差异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是故,我们在进行字词考证、章句释读时,必须慎之又慎,正如黄钊教授所言,“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拔高”,“对传世今本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贬低”[18]。试想,如果文本的校勘与考证完全借助于传世今本的引导,那么校勘很可能会带来文本“趋同”现象[19],而忽视帛书、简本异文本身的意义。反之亦然。因此那种追求古本或善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更加完整地理解老子的原始思想,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却在极有可能大打折扣,这也可以看作是文本勘察考订工作本身容易导致的局限。希望通过多个文本的互相订正,以塑造一个善本来理解和定型老子思想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文本考证最终还应该服务于研究文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所反映出来的“老子”思想的演变,这才是文本差异所体现的思想史、哲学史意义。 二、文体考辩与老子身世考证的现状与反思 上个世纪关于老子是否晚出曾经争论一时,伴随帛书《老子》、竹简《老子》的出土,《老子》晚出论已经不攻自破。但《老子》早期文本究竟形成于何时?老子究竟是谁?生活于哪个具体时期?老子故里今何在?近三十年来,对《老子》文体考辩以及老子身世的考证出现了一些新动向,说明学界始终没有放弃对上述问题的追问。 关于《老子》文体的考辩,上个世纪冯友兰、钱穆、顾颉刚、蒋伯潜等学者均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得出的结论是《老子》晚出。最近三十年来,通过《老子》文体考辩而论证《老子》文本形成年代的成果相对较少。刘笑敢先生延续了他在《庄子》文本考证方面的风格,对《老子》文体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诗经》、《老子》、《楚辞》的句式、修辞手法和韵式进行比较,他认为《老子》与《诗经》在多方面相似,而与《楚辞》相差较远,因此,“从《老子》的以四句为主的韵文句式来看,从它大量回环往复的修辞手法来看,从它多变而密集的韵脚来看,《老子》显然是在《诗经》的风格影响下的产物,而不可能是《楚辞》时代的产物。”[20]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考证成果在竹简《老子》整理出版之前,而竹简《老子》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证明力度。 韩国良先生考察了“箴”与“语”两种不同的文体,认为“《老子》在文体上属于‘箴’,《论语》在文体上属于‘语’。‘箴’的制作者是官师,‘语’的传播者是庶民。先秦诸子文体正是由先秦官方之‘箴’下移为庶民之‘语’,然后才渐次发展起来的”。除此之外,侯文华亦详细分析了先秦箴体的特征,认为《老子》是一部先秦遗留下来的箴体文献[21]。《老子》与《论语》以及战国中后期的很多其他文本相比,确实有自身的独特风格,如果文体的出现确实存在明确的先后之分,那么我们在考证《老子》文本形成年代方面又可以添加一种新的证据。据此,笔者认为韩先生等人的文体考辩成果理应受到重视,但这却无法得出韩先生所谓的老学研究“在文体考辨上,盲目疑古,以个人偏爱代替历史逻辑”的结论。毕竟,疑古思潮在近三十多年来已经不再是学术界的主流,尽管对孔子与老子孰先孰后仍然存在不少争论,也存在儒道研究者互黜的现象,但伴随简帛《老子》的出土,《老子》文本的形成年代得以前溯,老子的生活时期也进一步明朗,这一点学界研究颇多,毋庸赘述。韩先生于学界研究成果显然失察,因而以偏概全。 关于老子身世的考证,近三十年来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争议也十分激烈,分歧较大。下面分几种类型加以概述。 第一种考证类型,基本认可司马迁在《老子传》中的论述,着重考证老子生活时期、《老子》的作者以及孔、老关系问题,但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以詹剑峰、牟钟鉴、熊铁基、孙以楷、陈鼓应、白奚等人为代表,基本认定《老子》就是老聃所作。詹剑峰从《史记》、《庄子》、儒家典籍中考证老子生活于春秋末叶,老聃非太史儋,老聃李耳非两人,并制作了一个“老子年表”[22]。陈鼓应、白奚主张“老子约略与孔子同时而年长于孔子,《老子》书是老聃所作”,《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孔子思想受到老子思想的重要影响[23]。孙以楷则力主老聃作《老子》,太史儋与《老子》无关[24]。另一种观点形成于竹简《老子》出土之后,以郭沂、尹振环、张吉良为代表,主张将老聃与太史儋分别作为《老子》不同传本的作者,简本出自老聃,今本出自太史儋[25]。此观点标新立异,一经提出,学界哗然,孙以楷、高晨阳、陈广忠等人迅速展开了讨论。 第二种考证类型,不局限于《史记》的记载,甚至纠正《史记》中的一些讹误,旁征博引,着重考证老子故里,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老子故里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以刘庞生、杨宝顺、李水海、袁祖亮、王珏等为代表。这一派目前获得的支持较多,在实践中亦取得了较大优势。刘庞生分别考证了陈之相和宋之相,认为“相邑属陈不属宋”,老子是“陈、楚苦县厉乡人”,今河南鹿邑人[26]。李水海则分别驳斥了老子是宋国人的种种说法,认为老子是陈国相人,即楚国苦县人,今河南鹿邑人[27]。另一种观点认为老子故里在安徽省涡阳县,以孙以楷、王振川、杨光、廉成荣等为代表。孙以楷对《史记·老子传》进行质疑,考证出老子不是楚苦县人,而是宋国相人,即今安徽涡阳县境内[28]。王振川则在《老子与范蠡》、《老子庄子故里考》两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各种历史地理文献,认为“汉苦县也就是隋谷阳县,唐宋时的真源县,现在的涡阳县”[29]。这种考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均很大,然而时至今日,两派互相辩难的论文多达数十篇,持续论争亦有二十多年,仍无法达成共识。 第三种考证类型,着重考证老子的姓氏。关于老子姓氏,历史上已有不少考辩,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对传统观点有继承亦有发展,主要观点有“老李音转相通说”[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