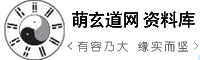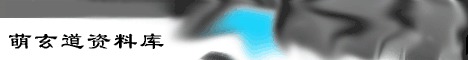近三十年来《老子》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述评——兼与韩国良先生商榷
韩国良先生在《孔子研究》2010年第4期上发表了《三十年来老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反思》[①]一文,文中,韩先生对最近三十年来老学研究大加鞭挞,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般来说,对某一课题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学术论文,应该充分掌握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详加考辩,分析剖判,然后予以公允之论断,否则就是空谈泛论,自说自话。反观韩先生的大作,显然有此嫌疑。该文不仅对老学研究的现状概括不准确,并且其所举的一些文本存在严重的误读。事实上,近三十年来老学研究在文本考证、研究方法、思想研究上均取得了较大突破,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老学”概念过于宽泛,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对老子研究的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进行评述,以求教于韩先生与学界同仁。 一、文本考证上的成绩与反思 文本考证是义理诠释的基础,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规范,于今已成学界的共识。然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老子》文本考证仅仅局限在传世的各种文献中,材料所限,因而进展并不很大。近三十年来,随着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郭店竹简《老子》的先后出土,老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文本考证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通常广义上的文本考证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文本的结构、章句组合、文本性质的考证;(二)、文字释读、校勘、词义考辩;(三)、文体考辩;(四)、文本作者的考证。本文将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当作狭义的文本考证先加以分析,后两个方面的内容则放在下文独立分析。 从文本的结构、章句组合、文本性质方面来看,学界充分关注到帛书、竹简《老子》抄写者留下的各种章节标记以及抄写的顺序,尤其注意到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之间的差异。关于帛书《老子》、竹简《老子》、通行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主要有模型说、阶段说、特征说。罗浩提出了“辑选模型”、“来源模型”、“并行文本模型”三种模型说[②]。李若晖针对整个《老子》文本的演进提出了“四期说”,即形成期、成型期、定型期和流传期,其中郭店竹简《老子》处于形成期,而帛书《老子》则处在成型期[③]。刘笑敢先生则从版本特征与文本内容特征角度,提出了“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的观点,以此解析老子文本的演变特征[④]。 从文字释读、校勘、词义考辩方面来看,学界以帛书、竹简《老子》校勘通行本,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结合帛书较早进行《老子》文本注释的有任继愈、陈鼓应、许抗生、黄钊、郑良树、高明、张松如等学者。而围绕竹简《老子》,李学勤、裘锡圭、何琳仪、李零、丁原植、陈伟、刘信芳、魏启鹏、尹振环、廖名春、刘钊、陈锡勇、刘笑敢等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此外,新近出版的丁四新教授的《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更是汇集诸家研究成果,详加考证,进一步推进了《老子》文本的研究。另外,《简帛研究》、《简帛语言文字研究》、《楚地简帛思想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国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文字》等海内外学术集刊或网站上都推出了大量关于帛书、竹简《老子》文本考证、文字释读方面的论文。比较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显然文字释读、校勘、词义考辩这一方面的成绩更为突出。 尽管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当中,学界仍然存在着不少分歧,但正是借助这种研究,学界在《老子》研究上仍然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老子》的流传版本和形成时代有了新的看法。帛书出土将《老子》形成推进到战国中后期,而竹简《老子》则表明《老子》抄本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流传[⑤],甚至可以推进到战国早期和春秋末年[⑥]。尽管目前关于简帛《老子》与通行本之间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但竹简《老子》应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老子》版本,帛书则是较早而又较为完整的版本之一。上个世纪疑古思潮影响下《老子》晚出的结论不攻自破。 第二,竹简与帛书提供的《老子》文本,不仅具有版本学意义,同时具有思想史意义。通过文本的校勘,简帛中一些重要字词的考释为订正通行本中的文字讹误提供了基础,如王弼本第21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中的“降”,帛书甲、乙本均作“俞”,竹简本作“逾”;再如王弼本第15章首句作“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帛书乙本作“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达”,竹简甲组作“古之善为士者,必非(微)溺(妙)玄达”。这些字词的订正通常并不影响义理诠释,但古本《老子》的版本学意义不容忽视。而有些文字差异则影响到义理的诠释,如竹简中并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从而引发对早期儒道关系的重新考察;竹简中“天下之勿(物)生于又(有)生于(亡)无”中并不重“有”字,由此引发对早期老子思想中“有”、“无”关系的思考。这些差异显然具有思想史意义。 然而韩先生却认为近三十年来老学研究“在文字校勘上,停滞不前,对老子经文缺乏深入的考证”,事实上,这种论断根本经不起推敲。通观作者全文,除了以帛书、竹简文本为基础并引用张松辉的《庄子疑义考辨》一书外,再没有一处直接或间接提及近三十年来学界的校勘考证成果,怎可如此草率地得出“停滞不前”的结论呢?且看韩先生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几个例子。先看争议不断的第1章[⑦],竹简《老子》的出土并没有消除这种争论。但“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两句经文无论如何断句,也不应该有韩先生所谓的“在万物之前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万物之始’,一个是‘万物之母’”的结论。因为不论是以“无名”、“有名”为句,还是以“无”、“有”为句,这两者都不过是“名”而已,并非两个独立不同的实体性存在物,因为这个“名”所指之实都是一样的,故下文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帛书作“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不管是“无名”、“有名”,还是“无”、“有”(本文以无、有断句),都不过是用来描述那个常存之“道”的“名”。诚然这种理解似乎和通行本“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相违,即“无”似乎比“有”更为根本,但较之于竹简《老子》第41章的“天下之勿生于有,生于无”[⑧],至少从形式上可以说天下万物既生于有,也生于无。这里的“有”、“无”均是老子所命之名,“名”虽不一样,但所指实质相同,都是指生天地万物的“道”。 而韩先生从通行本中读出矛盾,并依据竹简第41章,认为“首章必应是‘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又)名万物之母也’的讹误。其中的‘有’应该读作‘又’”,并且认为学界“仍然读‘勿’为‘物’,并未把它看作否定词,如此老子首章的经文就仍然讹误着”。 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又”与“有”可以互通,先秦文献中确实常见[⑨],帛书中很多“有”写作“又”,如帛书乙本“众人皆又余”;竹简中也有不少,如“又亡之相生也”。古汉语“又”可作副词,意为“复”[⑩]。但这里的“有”是否可以通“又”呢?显然不行。因为“名”总是和“实”相对而言,“无名万物之始”中的“无”是主词,是被老子用来命名“实”(万物之始与母)的一个“名”。如果老子在第1章只用一个“名”来表达天地万物之“始”与“母”的观念,那么“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中的“此两者”何指?“异名”又何谓?也许有人会说,王弼的注表明此两者是指“始”与“母”,但要注意王弼是以无名、有名为句读的。因此,“始”与“母”两个表达万物初始的观念在句中都是处在“实”的位置,尽管它们本身也是一种“名”,但在此两句中,仍然要用“无”、“有”两个处于主词地位的用来指实的“名”来表达。如果将“有”消解,那么对应的“此两者”就变成了“无”一者了,导致经文前后矛盾。韩先生追求将“无”作为老子的根本观念,消解了此处“有”作为独立哲学观念的地位,显然不合理。 其二,“勿”在这里作否定词理解是否合理?韩先生批评学界“仍然读‘勿’为‘物’,并未把它看作否定词”,莫非将“天下之勿生于有,生于无”解读成“天下并不是从有生出的,而是从无生出的”?将此处之“勿”解读成否定词,实在是匪夷所思。《老子》本文的一个特征就是章节短小、语言精练,很难想象老子本可直接陈述天下万物生于有或生于无的主张,却要转弯抹角先否定,再肯定,即天下万物不是生于有,而是生于无。这种“不是…而是”的转折表达风格在《老子》文本中没有旁证,完全是现代人的臆想。韩先生过于追求老子哲学中以“无”为本的所谓一元论观念,标新立异,以致有扭曲文本的嫌疑。 韩先生将“无”确立为老子哲学中的一个根本观念,并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有”是相对的、生灭的、有条件的,它们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在此基础上,他将老子第2章中的“故有无之相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