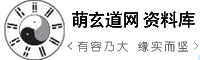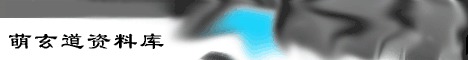《太玄》对“易”“老”的会通与重构
|
《太玄》每两赞主一日,七百二十九赞则主三百六十四日半,外加踦、赢两赞而满一岁之日数。故《玄图》云:“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满焉,以合岁之日而律历行。”汉初,袭用秦之颛顼历,但逐渐发现它已与实际天象不合。因颛顼历定一岁之日数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日之一,而此日数是有误差的,所以到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主张改正朔、制新历,于是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同时遴选长于治历的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二十余人创制汉历,因此年为太初元年,故又称太初历。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特重历元,所谓历元,就是以冬至恰好是甲子日甲子时之朔旦,作为推算历法的开始。太初历的制定,就是“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汉书·律历志》)而具体的运算转历是由邓平、落下闳完成的。邓平创制了八十一分律历,定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一岁的月数为十二又十九分之七月,一岁的日数为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玄告》云:“玄日书斗书而月不书,常满以御虚也。”这是说,日行有常而无亏,斗柄所指有定向,故可书;而月有赢虚、所行不常,故不可书。《玄告》又云:“岁宁悉而年病,十九年七闰,天之偿也。”叶子奇注谓:“岁道常舒而有余,故无忧。年道常缩而不足,故有病。是以十九年而置七闰,以偿还其不足之数也。”(《太玄本旨》)叶注语焉不详。对此,俞樾诠解甚精。他说:“日躔黄道一周,历春夏秋冬四时,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为一岁。月离白道一周,历朔望晦,后追及日而合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为一年。岁与年较,多十一日弱,所谓气盈也。年与岁较,少十一日弱,所谓朔虚也。……自立春至大寒,而岁实始尽。然正月朔日立春,至十二月晦日。尚未至大寒,是‘年病’也。病者,病其不足也。于是三年必置闰焉。故下文曰:‘十九年七闰,天之偿也’。”(《诸子平议》) 太初历后刘歆加以推究和整理,是为三统历。刘歆以《易》推历以说《春秋》,企图为太初历建构理论根据。所谓三统即天统、地统、人统,天统始施于子半,地统受之于丑毕于辰,人统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汉书·律历志上》)《太玄》以太初历(三统历)为基础,创制了一个特别的历法,蕴涵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故云“玄之道也”。邵雍曾说:“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皇极经世·观物外篇》)此评至为精当。 扬雄的太玄图式亦吸收并改造了孟、焦、京等人的卦气说。《易》之卦气起中孚,坎、震、离、兑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节气,即坎卦自初爻至上爻主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六个节气,震卦主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六个节气,离卦主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六个节气,兑卦主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六个节气。其余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六十卦配七十二候,尚缺十二卦,则以候卦补之。就一年的节气变化说,十一月中冬至,初候为公卦中孚,此为一年节气变化的开始,至次年十一月节大雪,末候卿卦颐为一年节气变化的终结,周而复始。《太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赞,一赞为昼,一赞为夜,合二赞为一日。八十一首,凡七百二十九赞,合三百六十四日半,外加踦、嬴二赞,成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日之一。中首初一,冬至之初也,踦、赢二赞,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复始。《太玄》首名皆以《易》之卦气为次序而变其名称,如,《玄》之“中”,《易》“中孚”也;《玄》之“周”,《易》“复”也;《玄》之“少”,《易》“谦”也;《玄》之“戾”,《易》“睽”也等等。故《玄首都序》曰:“八十一首,岁事咸贞。”《玄测都序》曰:“巡乘六甲,与斗相逢,历以纪岁,而百谷时雍。”按,日右行而左还,北斗左行而右旋,在牵牛一度半建子位,日斗相逢,各一周天。故称日行乘六甲,周而复始,以成岁事。另外,《太玄》还将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配以二十四气和日躔宿度,以及风雨物候,用以说明四时季节和月令的变换。故《玄图》云:“阴质北斗,日月畛营,阴阳沈交,四时潜处,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轸转,驯幽推历,六甲内驯。九九实有,律吕孔幽,历数匿纪,图象玄形,赞载成功。”即是说,《太玄》包含有以北斗指向定时,日月循其轨道周行,阴阳二气消息盈虚,四时节气交相更替,五行旺伏更相用事等;还包括天体浑沌,星宿运转,推求历法,时日纳配干支等。故叶子奇云:“此备言《玄》配合乎斗、日、阴阳、四时、五行、六合、七宿、六甲,莫不俱于八十一首之中,以至律吕、历数亦莫不藏其纪度,所以玄图莫不传著而昭列焉。”(《太玄本旨》)但是,《太玄》毕竟不是天文学和历法,而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只对天文、历法等予以理论的说明,使之从具体的自然科学升华为世界图式,而不能代替具体的历法和天文学。 四 《太玄》是拟《易》之作,同时又吸收了老子的天道观和辩证法,因此是会通《易》、《老》的杰作。但就运思理路而言,《太玄》明显地近于《老子》,而与《周易》有所不同。《周易》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直至六十四的二分法,将八卦与六十四卦联为两两相对的整体,它把阴阳视为两体,故而两体的“中和”、“中介”不易透显。《太玄》则不同,它以三分法代替了《周易》的二分法,强化了阴、阳的结合体即阴(一)、阳(二)、和(三),凸显了阴阳参和、阴阳消长的调节功能。此思想可溯源于老子。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只有“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架构,才能昭示“阴阳一体”以及阴阳在一体中的“参和状态”。在扬雄看来,这种参和状态表明“玄”是与阴阳共存而兼制阴阳的共体。他说: 莹天功、明万物之谓阳也,幽无形、深不测之谓阴也。阳知阳而不知阴,阴知阴而不知阳。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玄摛》) 这是说,玄是非阴非阳,即阴即阳,即主阴又主阳的阴阳浑一体,亦可谓阴阳共体并兼制阴阳的关联者。叶子奇云:“阳主息,变物而有形。阴主消,化物而无迹。然阴阳,气也,故局于一偏而不通。玄者,理也,故通于两端而兼体。”(《太玄本旨》)譬如,天、地、人作为三才之道,《周易》中只能以六爻“兼三才而两之”来体现。而《太玄》则不然,“夫玄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玄图》)所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方州部家皆以三起而成四位也。 《太玄》完成了《周易》符号模式的重新改组,显示了它多层面涵义的优势。《太玄》三分法的优势主要凸显于两个方面:其一,它把事物共同体的全貌概括了出来。作为共同体不仅有“阴”与“阳”的对待,而且有维系这种对待的“叁”,即通于“阴”“阳”而兼体的“和”。质言之,既没有纯粹的独阴,亦没有纯粹的独阳,阴阳局于一偏皆不通。其二,在事物共同体中,“玄”(和)起着维系全局的作用。阴阳相错相行,阳息阴消,阴息阳消,无论是阳的动吐,还是阴的静翕,都表示旧事物的减损与消失,新事物的增长与发展。尽管阴阳有更迭,事物有演化,而“玄”(和)的维系作用并不因此而消亡。正如《太玄文》所云:“罔蒙相极,直酋相敕。出冥入冥,新故更代。阴阳迭循,清浊相废。”而“罔之时,玄矣哉”。由此可见,《太玄》的三错符号“—”、“--”、“┄”弥补了《周易》二错符号“—”、“--”的不足,更能体现尚中的“中和”之道。 然而,《太玄》并没有取代《周易》,它的地位和作用更不可与《周易》同年而语,这是为什么?概而言之,不外乎《太玄》的文字艰涩深奥,一般士人难以理会其意旨,就连宋代的大学者司马光尚须“读之数十过”,方能“稍得窥其梗概”(《太玄集注·读玄》),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当然是可想而知了,此其一。《周易》的“经”和“传”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两者之间差异很大,“传”本于“经”,然而更是空前地升华了“经”,因此无论就其学说建构、思想内涵抑或学术层次,都存在着明显的、根本性的差异。从《易经》到《易传》是人类思维冲破占卜樊篱而升华为哲学理论的进步过程。可是扬雄的《太玄》却将自己的理论硬性地纳入早已落伍的占卜形式之中,禁锢了理论的生机,因此《太玄》企图借用占卜形式以建构其体系是失败的,此其二。 不过,就创立新的哲学体系而言,《太玄》是扬雄的潜心精思之作,没有《太玄》扬雄就称不上是一位有个性的哲学家。正是这种哲学个性,使之对魏晋玄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太玄》的建构形式虽说不成功,但它对神学经学的背离和挑战,以及它对事物现象背后深层本质的探索,深深地启迪了魏晋玄学,为后一时期辨析才性与玄理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高潮的到来,起了铺垫作用。又因《太玄》是《老子》和《周易》相结合的产物,胡汉末的解《老》注《易》诸家,如宋衷、虞翻、陆绩,都熟谙《太玄》并为之作注,为嗣后《易》、《老》、《庄》三玄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条件。 总之,《太玄》一方面希冀取代汉代经学而又未能予以取代,另方面它想超越烦琐的象数之学向思辨哲学发展而又未能达到魏晋玄学的高度,从而成为两汉哲学向魏晋玄学转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 |
查看所有评论